《心经》的现代意义与普世价值
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,西行取经路上,步步有灾,处处有难,性命危在旦夕,幸得三头六臂的孙悟空保护,历时十七年,通过九九八十一难,总算从佛祖的家园——天竺,取得真经。人们公认孙悟空是一个三头六臂的精灵,因有七十二种改变和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的本领,上天堂、入地狱,来去自如,手持如意金箍棒,配上一双火眼金睛,除妖惩恶,为所欲为,无所不能。那么,孙悟空的“法力”来自何处?答案就在他的姓名“悟空”中。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以参禅的三重境界来阐释悟空的三个层面:(1)参禅之初,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
(2)禅有悟时,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(3)大彻大悟时,看山仍然是山,看水仍然是水。山水仍然,但随悟道者“有我”、“无我”和“忘我”之深化,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随之而改变,终究取得心无挂碍的人生。
“有我”时“患得患失”的人生
《西游记》的灵魂人物孙悟空因三头六臂而心高气傲,自我无限膨胀,一闹龙宫,二闹鬼门关,三闹天宫,终究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多年。《心经》指出,修行之前,世人和孙悟空相同,误以为“我”为实有,世间的名、利、美貌等都是实在不虚的,“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”,处处执着;有执着,便有挂碍;有挂碍,便会患得患失,不安、恐怖之心随之而起:放不下对自己不公平的人和事,憎恨心生起,使人活在不平、痛苦与挫折感中;放不下自己的失误、失败,懊悔心生起,令人活在暗影中;放不下自己的成功与荣耀,贡高我慢之心冒起,使人在骄傲中逐步阑珊;放不下自己喜爱的东西,贪爱之心生起,于是便想方设法,甚至不择手段、自私自利、离心离德去得到或保卫自己喜欢的东西,从而引起家庭、公司、社会间的种种胶葛与抵触,使得人间处处充满险峻、纷争和不平,使得身处其中的人烦恼重重、痛苦不堪;放不下自己的意见、观点、主张和理论,固执己见之心生起,让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有机可乘,以各种托言挑起争端,使无数无辜的生命受到伤害!这些苦难,正是《心经》所要解决的问题,即“度全部苦厄”。
“无我”时“看透放下”的人生
在一般人看来,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是位标准的无用好人,但他有相同本领,只要念观音菩萨密授的紧箍咒,三头六臂的孙悟空便随声倒地,头痛欲裂,不得不跪地求饶。“紧箍咒”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?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?据史料记载,一天玄奘法师在取经途中,看到一个身患流行症的老者,长了一身癞,正在呻吟,他停下来照顾这位患者。患者为了感谢他,就送他一本梵文的《心经》。从此之后,玄奘大师在路上一遇到困难,就念《心经》,一路消灾免难。由此我们不难推断,紧箍咒的内容其实就是《心经》的核心要义——悟空。
《金刚经》云:“全部有为法,如梦幻空想,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。”这首偈语告知人们,人生如梦,苦乐如空想,胜败如朝露,荣华富贵如浮云,功利如镜花水月,宇宙间万事万物瞬息变幻,无时无刻不在改化。若能领悟到全部万法的本质都是空无自性,执无可执,看自我、苦乐、功利、美色时便能到达“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
水”的境界,取得破透放下、洒脱自在的人生。
忘我时“心无挂碍”的人生
《心经》以“空”来破除人们对自我、身外之物和各种理论的执着,但是佛陀说“空”之本意,不是否定宇宙万有的存在,不是“虚无主义”,而是为了破除人们的执着。换而言之,“忘我”不是否定自我的存在,而是领悟自、他不二的联系,就能摆正自己与别人之间的联系。好像把自己看成是一块盐,放入水中后,“盐”不是没有了,而是融于水中;同理,一个人若能将自己融于群众,便能领悟自、他不二之妙用,泯除人我的对立。如此人们便不再执着于是非人我,不再执着于自己的观点、见地,超越相对、相待、差别相,入不二法门,以随缘的心态去做有益之事,山仍然是山,水仍然是水,只是山水的形色早已了然于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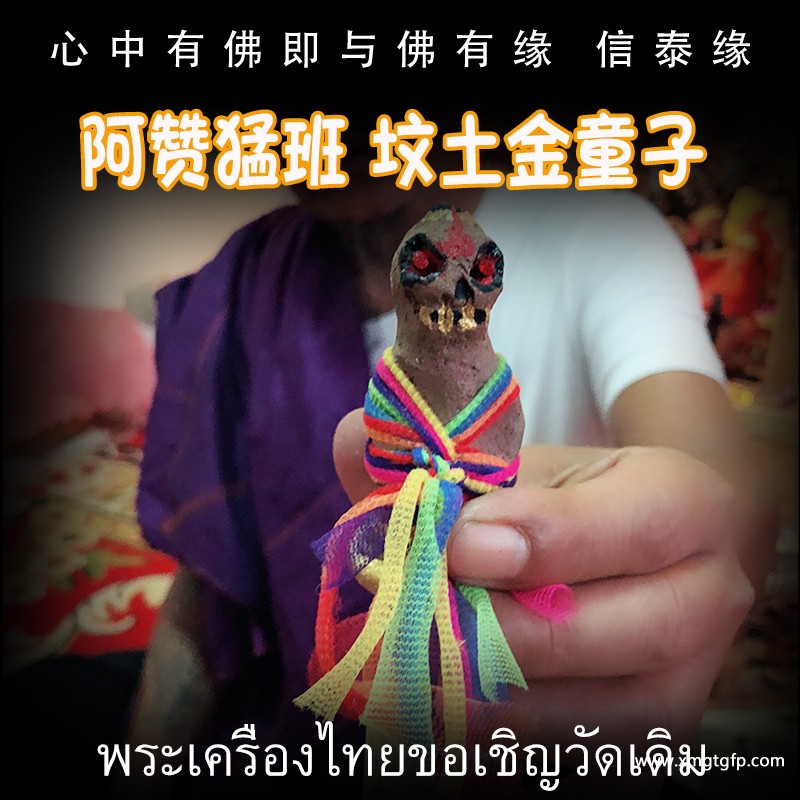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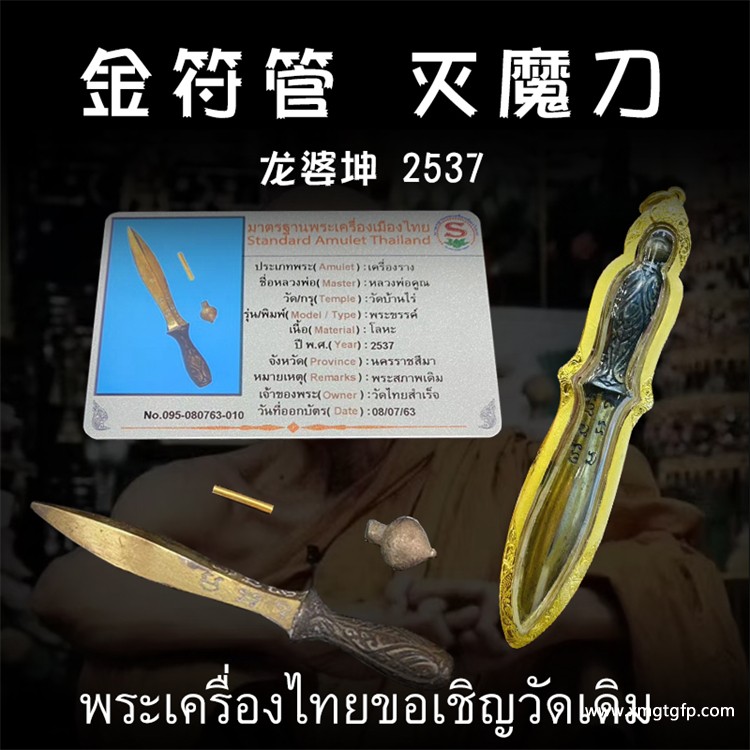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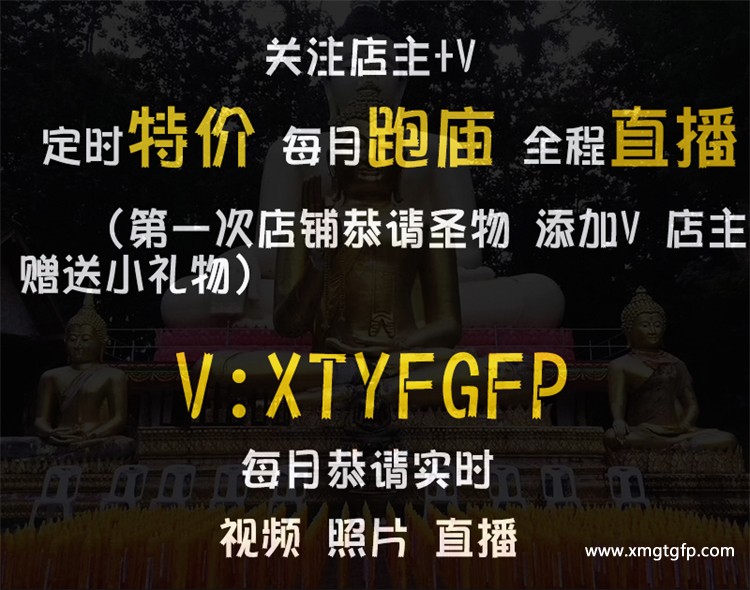
 在线客服
在线客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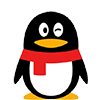 在线客服
在线客服